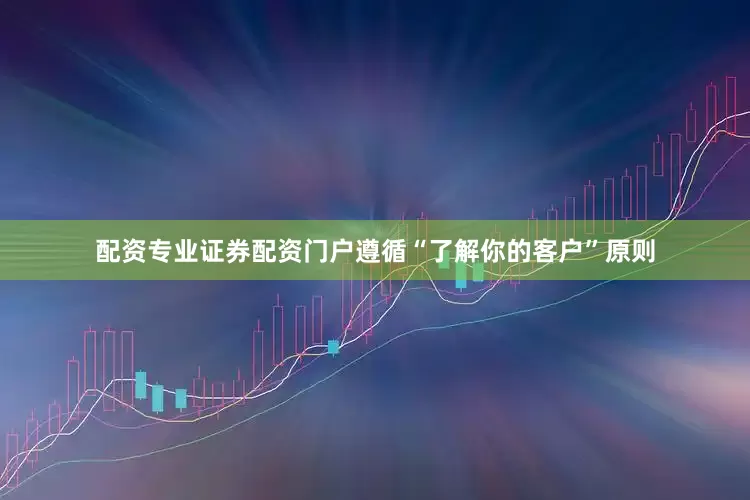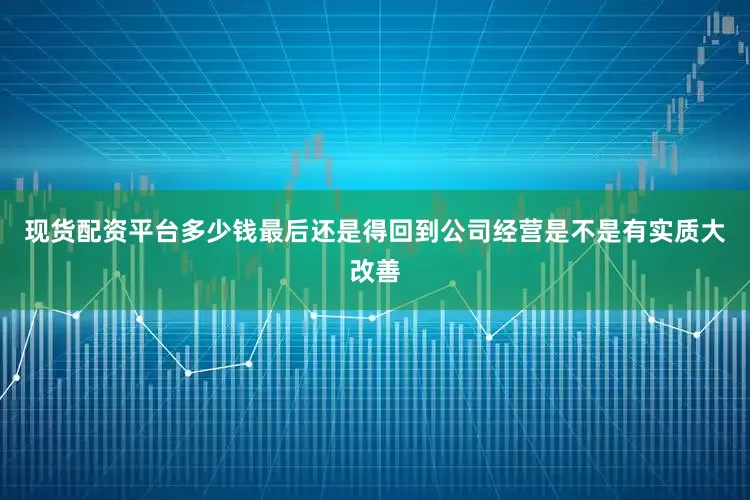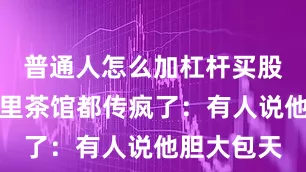
1930年洛阳旧营房里的霉书与冯玉祥42万兵败的前前后后
洛阳西南的那片旧军营,春天潮气重得很。仓库门一推开,味道冲得人直皱眉。几个年轻兵在里头翻找废物,有人从角落扯出一捆发霉的小册子,封皮印着“信仰整军”四个字。扉页墨迹还算清楚:“整肃军风,重在心诚”,落款是冯玉祥。一个河南口音的小伙翻了两页,就撇嘴:“这玩意儿能当干粮吗?”说完把册子塞回去压箱底——那会儿,他们连午饭都没着落。

往前倒几年,这位“冯天子”可不是这个光景。他早年混北洋,从吴佩孚手下的一支杂牌起家,到1924年已经握着十万兵权,还敢在北京搞突然袭击,把总统曹锟关了,自封卫戍司令。这事做得干净利索,北京城里茶馆都传疯了:有人说他胆大包天,有人说他替百姓出了口恶气。
政变之后,他跟苏联搭上线,不光收枪收钱,还请来顾问教练部队、搞政治课。有老照片留存下来——西北军穿统一灰布军服、腰间系皮带,操场上喊口号像模像样。据当时一个驻陕记者写的日记,那些士兵晚上还要写思想汇报交上去,比学生作业还勤快。

可这些看似新鲜的东西,在战场上不一定顶用。西北军号称42万人马,但真打起来能顶住阵线的,也就六个师,而且散布甘肃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各地,全靠地方摊派和借贷养活。有些团平时自己种地养猪补贴伙食,一到开战就乱套——庄稼没人管,人也饿肚子。
冯玉祥本人信基督教,他给士兵讲《圣经》,劝戒烟酒脾气坏习惯,还有传闻他曾亲自端洗脚盆给伤员洗脚,被记者写进小报,说是“将帅如牧者”。但战争不是礼拜堂,那几年蒋介石正忙着北伐,他先观望,再顺势宣布支持,“联蒋反奉”,趁机收复洛阳郑州,又吸纳了一批奉系残部,一时间风头无两,“南蒋北冯”的话甚至飘到了天津码头边上的茶摊里。

问题也随之而来:部队越多越杂,各路将领心思不同;财政更紧张,苏联援助渐停;南京政府拨来的补贴杯水车薪。他只好推广所谓“士兵养兵”,其实就是让官兵自己想办法吃饱肚子。这种消息传到江浙一带,被讥成“农场大队”。

他的政治立场一直摇摆,不全投靠蒋,也不彻底融入国民党,对共产党更是忽近忽远。一边喊革命,一边又参与围剿红军,让外界摸不准方向。当时宁汉分裂,他试图拉阎锡山和李宗仁搞中间路线,可形势已不同往日——南京方面牢牢抓住党政财权,没有多少空间留给这种半独立派系。他学蒋介石清党整编,却缺钱缺威望,引发内部排斥,新老派系互相掣肘。

1929年底,全国整编风声起,他觉察自己可能第一个被削,于是联合阎锡山李宗仁打出护党的旗号,中原大战爆发。从渭河以东到黄河沿岸,都有人看到赶赴前线的大车辚辚。但等真刀真枪碰面才发现,对手准备充分:张学良率东北精锐南下,有重炮、有装甲列车。而西北军通信还是靠骑马送信,据老参谋回忆:“有次急令跑半夜,到达时阵地已经丢了。”

粮草更惨,有段时间运输断档,大批士卒只能挖野菜充饥。一位逃回灵宝的退伍老乡后来对村人说,他们甚至煮过树皮熬汤喝。此情此景,让不少基层指挥员动摇,不少连夜撤走或缴械求生。阎锡山见局势不好按兵不动;李宗仁托病迟缓援助,只剩冯硬撑,但撑不了多久。

1930年秋,中原大战进入尾声,宣传攻势配合军事压力,使得西北军全面崩溃。10月间他们退至潼关以西,再无力东顾。在陕西某处祠堂内召开的会议上,冯对几名亲信低声道:“我走吧,从此不问。”第二天消息放出去,人们才知这位昔日枭雄隐退田园。据地方志记载,当晚渭河北岸有百姓燃灯祭河神,说是送走瘟神,其实暗指战火终于离开家门口。

退隐后的他并未沉默,在天津租界办报纸写文章抨击南京政府,自称革命军人,希望留下理想主义者形象。但现实冰冷:旧部早已星散,多数改换门庭或归乡务农。《保定府志》民国续修本里提到,当年的一些营长后来成了县城小商贩,还会背地骂一句“大帅害苦咱”。

1933年春,他乘船赴苏联考察,又绕道欧洲接受采访,希望借国际舆论再度出现于公众视野。在巴黎一家咖啡馆接受访问时,据译员回忆他说过一句法语谚语,大意为“没有根的树注定倒下”。国内对此毫无波澜,那时候的新局面容不得再怀念过去的人物了。

多年以后,我在安阳遇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,自称年轻时曾替父亲赶骡车为西北军运粮。他笑呵呵地比划着手掌宽度,说那时候馒头像碗那么大,可没几顿就断供。“你问我咋垮台?馒头没啦呗。”听完忍不住觉得,这句粗话,比许多史书解释都直接透彻些。

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,仅供学习交流,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
迎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